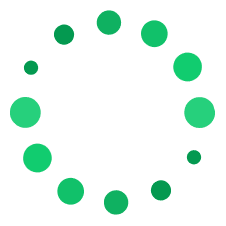[NOWnews今日新聞] 在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的長河中,張大千無疑是激起最壯闊波瀾的巨匠之一。有人稱他為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,有人驚嘆於他的多變畫風,更有人將他與畢卡索相提並論。這位橫跨古今中外的藝術大師,創作脈絡遠比常人想像得更為複雜多變,如同不斷翻新的藝術史詩,在傳統與革新之間譜寫著獨屬於自己的篇章。
張大大千曾表示,「不臨古不知古人用筆之妙,不摹古不知古人設色之精。」在他早期創作生涯中,臨摹古人是其藝術修煉的核心路徑。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,他沉浸於唐宋元明清各朝名家的筆墨世界,尤其對石濤、八大山人、徐渭等明清狂傑的研究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。
據傳,在張大千的畫室中,常能看到他將古畫擺在眼前,卻不直接對照臨摹,而是先反覆揣摩,待心中有數後才落筆。這種「熟讀唐詩三百首,不會作詩也會吟」的功力,使他在臨摹石濤時能「以假亂真」,令當時的收藏家和鑑賞家都難以辨別真偽。
1941年到1943年間,張大千在敦煌莫高窟度過了關鍵的兩年半。這段時光不僅改變了他的藝術視野,更深刻影響了其後半生的創作路徑。在昏暗的窟窿中,他臨摹大量壁畫,甚至不惜以身試毒,嘗試各種顏料的調配方法,只為還原敦煌壁畫的原貌。
從敦煌回來後,張大千的創作明顯展現出更為豐富的色彩感與構圖意識。他將敦煌壁畫中的濃麗色彩與古典人物造型帶入自己的創作,使其山水畫、人物畫都呈現出一種別具特色的華麗風範。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如《潑茶圖》、《丹崖碧嶂圖》等,都顯示出其對高彩度設色與大膽構圖的嘗試。
1960年代是張大千藝術生涯中的重要轉折點。隨著年齡增長和視力減退,他開始探索一種更為直觀、更具表現力的繪畫方式「潑墨潑彩」。
值得注意的是,張大千潑墨潑彩風格的形成,與他旅居世界各地的經歷密不可分。從香港到巴西,再到美國加州,這些異國風情與視覺體驗,都成為滋養其藝術創新的養分。特別是在與畢卡索會面後,兩位世界級藝術大師的交流更激發張大千對藝術本質的思考。
從1960年代開始,張大千的代表作如《廬山圖》、《春山煙雲》、《嵐光初霽》等,都體現潑墨潑彩的獨特魅力。這些作品既保留了中國山水畫的意境與格調,又呈現出一種現代感與國際化視野,為傳統中國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
與許多藝術家不同,張大千從不囿於單一風格。在他漫長的藝術生涯中,各種風格並行發展,甚至在同一時期創作出風格迥異的作品。從工筆人物到寫意山水,從傳統設色到潑墨潑彩,張大千的藝術世界如同萬花筒般絢爛多彩。
回顧張大千近70年的藝術生涯,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藝術家的成長與變革,更是二十世紀中國藝術面對現代化挑戰時的應對之策。從傳統到現代,從東方到西方,張大千的藝術歷程映射著中國文化的世界性對話。
在當代藝術市場上,張大千的作品屢創拍賣紀錄,《潑墨山水》曾以1.1億港元成交,印證市場對他的藝術價值高度認可。而在藝術史的長河中,他的名字已與石濤、八大山人等歷代大師比肩而立,成為中國藝術史上不可繞過的重要篇章。